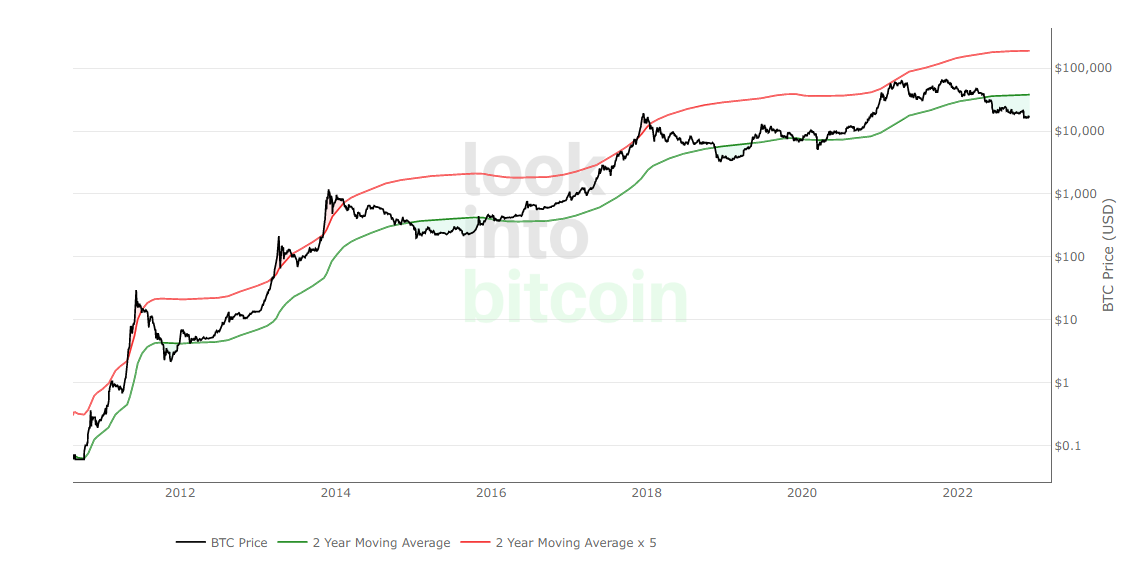2022年11月12日晚,由国家大剧院主办、多个线上平台同步播出的“行云流水”张维良笛箫埙音乐会在线上展演。音乐会曲目中,既有《楚歌》《梅花三弄》《夕阳箫鼓》等传统经典的改编与再现,也有《春潮》《行云流水》《飞歌》这些根据传统音乐元素创作的作品,还有《相逢》《顶嘴》这类融入爵士音乐元素的尝试,更有双笛呈现的《热情与冷漠的邂逅》。
如此曲目安排设计很“张维良”,是其50多年来“背靠传统,面向未来”理念的体现。
从苏州的街边巷尾中走来,竹笛一直与张维良相伴。在单调乏味的环境中,在巡演奔波的场地外,在获益良多的大学里,在蜚声世界的年华里,竹笛都给他撑起安静的角落。
 【资料图】
【资料图】
与此同时,他也不断为竹笛插上更多可能的翅膀。他饱览群书,为竹笛注入思想;他潜心学习,将西方音乐与竹笛巧妙融合;他多方尝试,把以竹笛为代表的中国民乐推向世界。
或许,他就是竹笛,竹笛亦是他。
1毛7分钱开启的旅途
将时光的指针拨回到2021年6月25日那个下午。张维良“梦境”独奏音乐会即将在苏州湾大剧院上演。
午饭刚过,坐落于苏州吴江东太湖畔的大剧院里一片忙碌,所有曲目都在紧张预演。距离演出还有四个小时,张维良开始针对灯光、现场声音、琴谱摆放、演员走位等问题逐一排查。下午排练时间总共三个小时,他一个人完成了所有调度。
这是张维良从艺五十周年独奏音乐会“梦境”全国巡演的最后一站。演出曲目里,《苏州湾》改编自他1981年创作的第一首作品《太湖春》。这一次,张维良带着60位小演奏家和学生合奏。倾听者正是张维良自幼生长的这片土地上的父老乡亲们。
时空交错中,一首老曲子完成了蜕变,当初的少年也已成为享誉中外的艺术家。
苏州是闻名遐迩的丝竹之乡。丝竹是中国古典乐器的总称,琴、瑟、笛等乐器都属于丝竹的范畴。茶余饭后,三五好友相聚,往往以丝竹演奏为乐。大人陶醉其中,孩童也不免好奇打量。耳濡目染之下,张维良对笛子产生莫名好感。
张维良六七岁时,三个哥哥姐姐都已有了一技傍身。大哥大学毕业后当了老师,二哥做了木匠,姐姐做了裁缝。父亲就询问小张维良:“人要有个手艺,你选择做什么?”
“学笛子行吗?”
“为什么?”
“笛子好听,个头短小,往书包里一放就行。在学校休息的时候还可以拿出来吹吹。”
第二天,父亲带着张维良来到了人民商场。1毛7分钱买来的笛子,少年自此爱不释手。
那个时代,可供消遣的文艺曲目不多,但笛子的空灵,却带给张维良全然不同的体验,“最开始是对无趣生活的一种反抗,后来的岁月里,最是让我陶醉。”
最初练习的那些年里,每天早晨六时,本就古香古色的寻常巷陌里,张维良的笛声就把人们从苏州带回了姑苏。
几年勤学苦练后,1971年,14岁的张维良考进了苏州吴县文工团,成为一名笛子演奏员,“那时候,我就开始挣工资了,一个月二十一块五。”
从那时起,张维良跟着剧团走遍了江浙一带的城镇乡村。其他演员闲暇时聊天,他则对当地曲艺满心好奇。几个剧团聚在一个院子里,他就跟着资深演员学艺;听说某地有名角儿,他打听到地方,趁着休息空当儿就跑过去拜望。几年下来,张维良濡染了苏州评弹、沪剧、越剧、锡剧,乃至昆曲。
“那几年我接触和吸收了大量民间音乐、戏曲音乐的营养,它们直接影响了我后来的创作。”张维良说,这个过程中于他影响最大的,是遇到了职业生涯乃至人生的第一个重要的老师——赵松庭先生。
“我小时候学过一本书,叫做《赵松庭的笛子》。”我国笛子演奏分为南北两派,北派梆笛音域较高,吹出的曲调粗犷、明亮而刚劲;南派曲笛则以典雅、唯美和柔和见长。赵松庭就是南派笛艺的代表人物,有着“江南笛王”的美誉。
“我起初跑到浙江歌舞团却扑了个空。”张维良几经打听才得知赵先生家的具体位置。1972年的一天,张维良带着小马扎坐在一艘开往杭州的小船上开启寻访之旅。12个小时的船程后,他见到了从艺之路上第一位重要的老师。
收徒的过程持续了三个月,实则是赵松庭对眼前这个少年进一步的考察。拜师学艺后,真正的辛苦接踵而至。
首先是舟车劳顿。三年间,张维良要时常往返于苏杭两城之间。为了省下钱给师父买烟,张维良有些路还要步行。其次是基本功的练习。赵松庭对学生的教导格外用心,抓住音准、节奏一些基本的音乐元素进行训练。
最让张维良意外的是,赵老师开出了数理化、律学、声学、考古学等十三门课。面对迷惘的少年,赵松庭解释道:“你不能光吹笛子。若止步于作一个艺人,你是达不到很好水平的。”
啃书的过程一点不轻松,但张维良的勤奋还是得到了老师的认可。
今日之成就也反过来证明了老师当年的教学方法是正确的。几十年后的太湖畔,张维良将从艺50年的成果汇报给家乡父老。笛声悠扬,带领人们感受鱼米之乡的水草丰美。街角的丝竹乐队、丰富的江浙曲艺、老师的谆谆教诲,都滋养着这位“笛箫圣手”。
手握竹笛行走的一生
张维良从没想过吹笛子能带来多么丰厚的回报,可一支竹子却吹出了他一生中最灵动的声音。
2021年4月24日晚,凯迪拉克·上海音乐厅里,一曲《春风遍江南》响彻全场,雷动不绝的掌声为张维良从艺五十周年全国巡演上海站画上句号。
舞台上,穿着一身笔挺演出服、架着眼镜的张维良,身材壮实,步伐矫健,雄姿英发,十首乐曲一气呵成。张维良的竹笛艺术融汇东西,贯通南北。他把江南甜润的音色与华北豪迈奔放的笛风相融合,乐音延绵不断,犹如行云流水。
“我还是觉得竹笛更美,因为它更通国人心性。”手握竹笛行走一生,是张维良在充分反思后做出的选择,“这样的坚持,我差点因为不够自信而错过。”
他还依稀记得,那年那日,沿着上海市复兴路往里走,上海音乐学院后门门前水泄不通——中央音乐学院恢复高考后第一次招生的复试榜单将在下午三时发布,一段围墙竟被挤塌了。
那日,他正好拜访老前辈陆春龄。经老先生几番鼓动后,张维良终于答应在回去的路上顺便看看。可这景象给了本就没有信心的他放弃的念头。然而,结果令他喜出望外,“进去一看榜单,九个参加复试的人里,我排在第二个,反复确认身份信息后,就是我!”
虽然被录取了,但张维良对将来的路依然不甚清晰,直到入学。
“民乐系宿舍紧缺,我就被分到了作曲系宿舍。”张维良说。宿舍在篮球场旁边的一排平房里,屋子里有一架旧钢琴。下铺的舍友曹家韵练琴时,随便弹奏了一首《黄河钢琴协奏曲》。
“把我吓傻了!我当时连钢琴都没见过!”张维良听完弹奏后肃然起敬,“我说,‘哥们能不能再弹一遍?再弹一遍我站边上看’。那种激动和冲动,旁人可能很难理解。”
从苏州千里奔赴北京,尽管学校里的大部分陈设都是旧物件,但思想却最是包容并蓄。《黄河钢琴协奏曲》雄浑壮阔,也冲破了思想的局限。
张维良整个大学学习期间,时值中国开放的大门刚刚打开,很多西方文化涌进中国,对当时的知识分子而言是一种强烈的思想冲击。
“你所坚持的,未必一定是对的,或者说,连什么是对的,你都说不清楚。”张维良发现中国民乐的发展尚存大量内容缺失,比如没有完备的理论,如何去分析一个作品,如何看待音乐作品的表现……
在张维良看来,笛、箫、埙这几种乐器都是最具中国人文特征的乐器。它们历史久远,足有七八千年。“比如埙,声音一响,无论在得克萨斯还是在维也纳,观众一听就知道是来自遥远东方的乐器,而且没有任何乐器可以取代它。箫一吹,人们就可以想象古代文人一袭青布长衫,摇着一把芭蕉扇在檐廊里踱步,那种情怀境界全出。一旦这些特征丧失了,你的乐器就什么都不是。”
思考的结果就是,要赋予传统以时代性。张维良说:“我觉得时代性主要表现在音乐内容和内涵上,而不仅是舞台上的某种形式。西方现代音乐给我们提供了一种手段和可能性。但最终,我们要表现属于中国音乐的内容,表现中国人的思想。”
中国色彩与东方韵味
悠扬的笛声响起,太极拳表演者仿佛瞬间找到灵魂,身形、音乐与光影融合在一起……2008年北京奥运会上,精彩的太极表演将中国文化的天人合一理念阐释得淋漓尽致。行云流水、天人合一的太极神韵,通过电子音乐与笛子的配合,在灵性之中彰显大气与浑厚。
太极表演配乐的作曲及笛箫演奏者,正是张维良。“当时那个节目的音乐已经盲选过好几轮了,最后比较荣幸,张艺谋导演盲选了我的作品。”
整首作品采用了电子音乐,加上鼓和远处传来的笛声,极具空灵感。“我取了中国人‘道’的内涵。如果没有这样的思想作为最后那层内容,那么音乐乃至整个表演就失去了灵魂。”
走出大学校门的张维良早早就意识到,要将思考放进演奏中。
早在1986年,张维良就灌录了中国第一张激光唱片《箫的世界》,改编的古曲《秋江夜泊》《梅花三弄》等更是成为经典广为流传。从1981年的处女作《太湖春》开始,到近年的《咏春》《梦境》《忆故乡》《乐春》等多首作品,张维良以吴越文化为根,融合了黄河文明,更辐射了富有浓郁地域色彩的多个乐种。《茶诗》《殇》《琴箫佛曲》等一系列专辑,更是对中国文化、写意、禅意的追根溯源。
“当初赵松庭老师给我讲,只吹笛子是走不长远的。后来慢慢地,我对这点理解越来越深了。”张维良说,创作一部作品,思考的时长远远超出真正谱曲的时间,“创作来不得半点虚假。如果不能用你的真情、内心的感受,并从哲学、文学、美学等不同领域的概念去思考,这个作品是不可能打动别人的。”
1996年,唱片《天幻箫音》问世,直到现在依然是经典。“我想原因大概只有一个:箫吹奏出的每一个音符,它的空灵又无所不在的音色,以及传递出的每一个意象,都是国人才能理解的东西。”在他看来,极具魅力的箫音如行云在天空飘荡,如流水在大地盘绕,在充满灵性的人声和富有魔力的MIDI等多种复合音色的衬托下,一张中国色彩与东方韵味的作品诞生了。
这张被称为“极具东方韵味的新世纪音乐作品”的唱片问世前后,张维良和作曲家陈其钢、叶聪等人合作,在维也纳金色大厅、纽约卡内基音乐厅、伦敦巴比肯艺术中心等举办演出,渐次将渗透着中国文人精神的音乐,在世界每一处重要的音乐殿堂奏响。
民乐探寻的更多可能性
音乐家莱纳在德国的工作室里按下钢琴琴键,声音直接通过互联网到达张维良的耳机里。在相隔遥远的两地,两位音乐家通过互联网的形式合作完成了《朋友》。
去年,张维良原本计划和德国音乐家莱纳做中国民乐与爵士音乐融合的巡演。因为全球疫情的原因,导致计划搁置了,然而关于音乐的交流并没有停止。
张维良认为,爵士乐是世界性的,现代音乐、民间音乐、传统音乐,通过爵士可以脱胎出很多可能性。“莱纳非常喜欢中国音乐。我也很希望能和外国音乐家共同表现东西方乐器融合的作品,将我们的笛、箫、埙、二胡、琵琶等乐器结合在一起,展示给大家听。”
传统与现代如何融合?如何用国际化的语言思考和创作中国民乐,让世界听懂中国?是张维良几十年来一直在探索的问题。他不排斥任何新事物,说起创作、创新、挑战和可能性,他依旧保持着和年轻人一样的热情和冲劲儿。
1993年,法国长笛交响乐团创始人皮耶·伊夫·阿尔托邀请张维良为乐团写一首作品。他最终写了一首《春之梦》。
“我发现长笛的音色虽然美,但会有雷同感,缺乏个性。所以我回来就想:如果组建一个竹笛乐团,一定不会输给他们。”张维良的这个想法在脑海里保存了十多年。
2012年,放下行政工作后,他就立刻全力组建竹笛乐团。首演前,张维良请陈其钢过来提意见。后者听完后就对学生们感慨:“你们太幸福了!有这么好的老师在你们正青春的年华里,陪你们探索如此前沿的音乐理念。现在你们未必感觉得到,但对未来来说,你们现在的尝试是非常重要的,或许推动着整个民族音乐的前进和发展。”
筹备5个月后,中国竹笛乐团在国家大剧院首演,取得意想不到的效果。“我们的温柔细腻是可以和西洋乐的弦乐队媲美的。我提倡整体的共性就是个性,就是说,我们整体抱团形成的声响和声是我们的个性。这种声音是其他民族乐器或者西洋乐器无法模仿的,这就避免了以往民乐队里各自张扬,你不知道听谁的好的情况出现。”
此后,英国爱乐管弦乐团也来委约张维良作曲。《莽原》就是一首带有内蒙古元素的民乐作品。乐团前常务董事大卫·沃尔顿听后,告诉张维良:“我听了几十年的中国音乐觉得听不懂。但是今天听了你带来的竹笛乐团的作品,我全听懂了。”
这部作品的成功得益于多重音色的组合,十支笛子和西洋乐器结合在一起,音响很是震撼。
“所以我不断在探索一支竹笛、二十支竹笛、四十支竹笛和西洋乐器对话。民乐就是要这样不断探寻更多的可能性。”张维良认为,要让西方人听懂中国音乐,就要先去潜心研究,如何把中国的元素和风格,与西方作曲的技术相结合,去思考中国乐器的声音融入西洋乐器后将会产生什么样的效果……“在没写作品前脑子里就要有这些思考,不能抱着试一试的心态去写。只有通过不断地实践去探索中国乐器各种表现的可能性,让观众来检验,这样才能得出客观的结果。”
2012年,张维良在家乡母校吴中区胥口中心小学成立了“张维良竹笛艺术培训基地”。近十年来,一届又一届小学生拿起笛子,在音乐中成长。他们在全国竹笛比赛中屡有斩获,或考入中国音乐学院附中等理想名校。最重要的是,他们收获了和张维良当年同样的快乐。
“我们拿起笛子的时候,它不再是外来的一个物件,而是像身体的组成部分。”走到哪里,张维良都对笛子爱不释手,“笛子代表着一种蒸蒸日上的气韵。我们不仅要去传播既有的音乐,更要不断思考让音乐‘活着’的方法。这样中国音乐才能声声入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