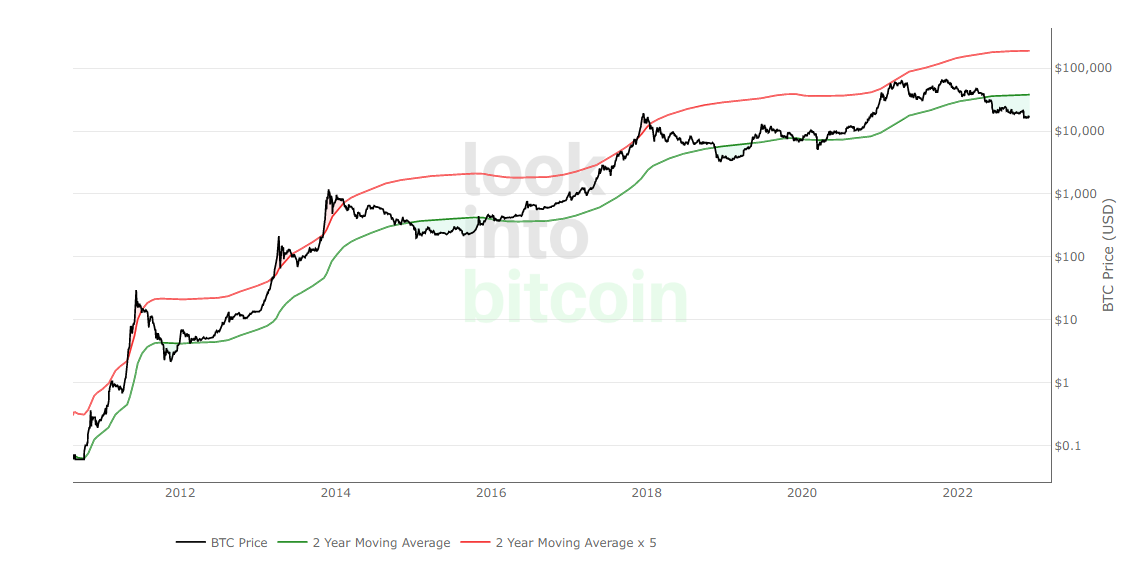展览:断裂的一代:90后的电子色、网络化、时尚消费、科幻散文和全球身份
 (资料图)
(资料图)
展期:2022.8.20-2023.1.4
地点:松美术馆
在充斥碎片信息的时代,文化似乎“难产”了,但当代艺术却造就了这样一批艺术家——他们开放、崭新且富有活力。由崔灿灿策展的“断裂的一代:90后的电子色、网络化、时尚消费、科幻散文和全球身份”延揽了十四位(组)艺术家:费亦宁、郭宇恒、侯子超、刘昕、马海伦、蒲英玮、史莱姆引擎、孙一钿、王梓全、袁可如、张季、张移北、张月薇、张子飘;由李佳策展的“转角见!——首届当下青年艺术奖”延揽了八位艺术家:麻剑锋、谭婧、王玉钰、xindi、熊佳翔、薛萤、袁中天、赵之亮。除赵之亮外,其他二十一位(组)艺术家都可以归类为90后的范畴,其中少数几位是00后。
1
想象一个代际、群体是一个具有挑战性的命题。考虑到90后的特殊性,我想它仍有待重审和回应。他们彼此之间的互文较以往的艺术家要少得多,与此同时他们又共享着差异性并不明显的“标准”。从整个文化领域而言,90后能够极便利地获取全要素的内在经验、技术、态度,不仅形塑了一代人的文化基础,还形塑了我们时代的文化基础。如我们所见,90后出现了超量的创意者、创造者,远非如今的文化产业所能承载。
上述艺术家几乎都来自城市中产家庭。1990年至今的城市中产家庭,一直以来都是文化生产和消费的核心场域,甚至是唯一场域。更为关键的是以“家庭”为核心轴的文化生产/消费逻辑如此强力地主导着艺术家们的成长、熏陶、教育、事业,乃至恋爱、婚姻。与此同时,“文化圈”“时代”“文化本体语言”等轴都被发配到配角的位置,后者可能什么也不是。何谓家庭呢?家庭教育和家庭学养吗?我以为不是。这个环境中的家庭指向的是父母对子女的权力关系:在父母的庇护和支持下,子女择一艺而自由,并从无论何种的现场退回到这一自由语境中,其中少数人几乎被随机抽取成为了创造者,成为了艺术家。这也是为什么县镇家庭、农村家庭极少出现创造者,因为它主要并非阶层决定的,而是文化决定的。创造者当然由于阶层差异而享受着完全不同的给养,但恰恰是从小圈层和大舆论中抽绎出的文化阻碍着基本的多元性、多样性的发生。
另一方面,从“85新潮”到“疫情时代”,社会环境和媒介环境已完全不一样,“85新潮”的艺术家们几乎必然带有自由精神、反抗态度、理想情怀等更像艺术家的面向,而“疫情时代”的艺术家面对撕裂、躁动的社会和舆论,其内生的个性、性格、态度被湮没了。在世界侵入私人领域的时代,借用维克多·雨果的话,“没有人有幸过着只属于自己的生活”,因此,我们时代的艺术家既是个性的,又是寻常的;既是反抗的,又是安静的。由于“单向度”文化、“内陷”世界的存在,艺术家们不得不向内探求,创造“第三人称/视角”自我。所以,私人生活的方方面面成了部分艺术家最重要的命题,艺术家们也不再希望生活和世界“一一对应”,而观众进入艺术家设想的家庭议题,也会感到它几乎无所不包。
2
从伦敦建筑联盟学院毕业前,袁中天意识到个人的焦虑和集体叙事息息相关。在创作毕业作品《边境怪谈》时,袁中天将自己的关心倾注到美墨边境,以物种变化、民间故事表达美墨边境的复杂——就像他喜欢的学者骆里山所说,在历史上,身体和土地的亲密建立在殖民贸易的基础上,在这种情况下,关系是令人不安的,甚至是暴力的。袁中天希望将个人的困惑,以及个人与外界的格格不入理性化,情感和记忆在这个过程中扮演着催化剂的角色。他的作品或因记忆、或因事件、或因关系而发生,但又走得足够远,比如缘起于母亲王清丽《泸沽湖组画》的《亲近更近》就勾连了亲密关系、定居殖民主义、母系制度、旅游业和艺术市场。
谭婧的《阿雄出走了》缘起于上世纪50年代归国的祖父母。小时候祖母经常谈起泰国的生活,祖父则沉默寡言,有次祖父带一只小狗回家欣喜得反常。在这个影像中,祖父的灵魂进入了一只小狗的身体。小狗打开感官,带来了老家旧屋、90年代在深圳园岭的家,充满东南亚风情的地砖则将观众牵引到往事的深处。谭婧喜欢改编、重映那些旧事:她曾以“田螺仙”对诸多母题进行了探讨,比如偷窥、掠夺、复仇、报恩、人与非人的禁忌、自然与女性的他者化……
薛萤的虚构叙事更为简约:她给女童配上宠物狗、文字“HAPPY”;给男童配上文字“世界”“足球”;以漏勺、电视机、蒸笼布、人工养殖珍珠贝壳抓取女人生活在“以男人为标准值,预设值”的现实中所经历的“排异,病变”,以此来质疑人类社会的结构命题。她曾在一次个展中发问:“何为家?家为何让人伤心?女人在哪里?她们为什么在那里?谁从她们身上受益?她们对自己的处境有什么话要说?”
费亦宁用影像《歧路故事I:外祖母》讲述一个走向终结的仿生人试图走进林木深处与菌根网络相连,并最终以单性生殖的方式迭代出“我”所在的阴性族系的故事。外祖母的身体与单花锡杖花共生,而单花锡杖花完全依靠菌根而生,他们都发生了形变。而费亦宁在虚拟世界捏的泥巴恰好表达了变化的暧昧、无限,就好像哲学家唐娜·哈拉维提及的“与麻烦共存”。小时候费亦宁在小兴安岭看树或者天空看久了,就发现所看处不断生长出神经网络。于是她在影像里将极微观(菌丝)和极遥远(星星)的景象叠加——在星空的背景下,锡杖花消失了,显微镜下生长的菌根显现在天空,一切都开始发光。
新一代艺术家或者90后艺术家在祭祷他们所由来处时更加积极地挪用异域经验、寓言或蓝图,借此某种或称之为第三人称视角的形象产生了,艺术讲述着第三种故事——设想一下,“85新潮”前,艺术家讲述着中国的故事;“85新潮”后,艺术家在中国故事中加入了现代;而今天,艺术家则将现代前置——新一代艺术家就像这么一颗现代的落地的种子。
在谈论新一代的言论中,梁永安的发言颇值得回味。他视90后、00后为复仇的哈姆雷特,他们“实际上追求的是自己的归纳,要立足于自身的社会体验建立自己的判断”。在此基础上,他期待90后、00后成为“凿空一代”,像张骞一样去开拓西域,创造新的社会情感、价值观念。作为90后,我想梁永安的期待正在成为现实,但90后、00后显然无法成为复仇的哈姆雷特,因为复仇的选项早已经被取消了,或者说复仇也是继承的一部分。另一方面,90后、00后“改造”自身的途径并不是通过出使西域,而是通过从社会那里接手,他们知道世界有多大,权限有多大,这是一种很不一样的自由。不妨假设90后是60后、70后的幼体,90后之所以如此轻易地完成多种角色的无缝对接正来自于此,艺术圈的“毕业即职业”并不足为怪。
3
在高科技“卡脖子”成为僵局的当下,技术似乎成为人们审视一切的标准,看看舆论对待文化的态度就知道了,以通俗之证、“小圈子”之嫌挟持某一领域似乎已成为了不破的“真理”,且这种挟持早已渗入领域内的生态,遥控着创造的发生。就目前而言,人们的目光已经缩减到两人关系的内部,“卷”“躺”“润”虽涉及了社会的诉求,但大抵聚焦在我自身的境遇,通常关乎的只是父母子女关系、爱情或亲密关系,以及自我与自我的关系——我们也可以从社交媒体的表演性倾诉或者自语中发现这一点。但是,当代艺术领域似乎是一片例外之地,凭借自成一体的市场、机构、评价体系,当代艺术未必需要进入大众、通俗的命题中。
在其他艺术领域纷纷“内缩”“低沉”的情况下,当代艺术在新一代则添色不少。新一代艺术家虽无深度的开拓,却有极其强健的外表,或者狂欢式的表达。它来自极富足的生命,他们的作品告诉我们,似乎生命本身要远远重要、多彩于情感、思想等这些常论及的命题。在这个意义上,艺术家们无论使用的方法多么现代/当代,他们似乎都是古典主义的。
“这是个急功近利的时代,所以我要以暴制暴。你要颜色,就给你颜色;你要粗浅,就给你粗浅;你要欲望,就给你欲望;你要窥探,就给你窥探。没有什么可以遮掩,任何形象都可以是一座纪念碑。”二十岁出头看到眼花缭乱的低质内容,孙一钿早早定下自己的倾向,中国的“kawaii”,既超现实主义又现实主义的“kawaii”。她关注“物”,商品化的、成系列的、标准化的物——这些物有实实在在的,也有主观编造的。《狄俄尼索斯的沉迷Ⅲ》的玻璃珠就由淘宝8毛一颗的紫色弹珠、大螺旋星系(NGC123)纹理组装而成。孙一钿热衷于双联画,具象和抽象相互搭配,并置后语境微妙地波折和变化。更重要的是,这种蒙太奇的效果也体现在画面内部,由于物与物的组装关系,或者物内部的组装关系,蒙太奇使错位、分歧、裂解富有生趣。
在马海伦的影像中,色彩鲜艳的裙、花样繁多的家具与装饰、开放又精致的姿势,就像普通人热爱生活那般热情洋溢、生机勃勃。如今已是国际时尚杂志摄影师的马海伦深深记得,小时候邻居姐姐每次下楼就有饰品碰撞的声音,香水味摇荡,维吾尔族阿姨每次取钱款都会把裙子掀起,把长筒袜滚下去再把钱拿出来。18岁去纽约上学前,马海伦一直生活在新疆。在她眼里,新疆有一种不输于北上广的浑然天成的国际化。
我们时代的国际化曾被粗浅地理解过,那是一种有国境线的国际,而今天的则是没有国境线的国际——越来越多的艺术家在国际田野上恣意生长,并非身份的转变,而是内在语境的转变。崔灿灿注意到:纽约视觉艺术学院、英国皇家艺术学院、法国里昂国立高等美术学院、武藏野美术大学、帕森斯设计学院、伦敦建筑联盟学院使他们完成了艺术的“脱域”;他们耳濡目染了欧美当代艺术的动向和新潮,主动地在一个多重背景下创造了自己的方法和命题。细究下来,在多数艺术家那里发生的是,脱域并非完全主动的,而是紧跟时尚的。也正如李佳所见,新一代艺术家从创作、展览、社交等各个层面与“国际舞台”接轨,由此他们也经常被看作是全球公民、文化游牧者、世界主义代言人。
王玉钰使用的材料包括硅胶、发泡硅胶条、头发、吉他弦。起先她发现搭扣材料包装上印着“Hook and Eye of Collar”,“钩子”“眼睛”“领子”三个字赋予了她对感官的新想象。“三合板,脚手架,铝合金条,尼龙布,水泥墩,塑料板,电线,插座,砖头,粉红色的橘色的霓虹灯管。”她曾在一次个展中自述,“写着欢迎光临的地垫:这里便是通向乐园的入口。”对媒介、物的占用和串联最终达到了酣畅淋漓的效果:这是开始于千禧年的故事,物在没有符号化的时候就享有了自身的所有因果,等你来到它面前,它就开始为你表演它的故事、它与你的故事。
00后郭宇恒从小就喜欢相对平面的纸人。她接受不了立体多维的真人,也接受不了cosplay,除非是kigurumi(穿戴玩偶)。14岁开始,她爱上了一个动漫人物,恋爱的日常就是想象自己处在“异世界”和他互动,和他的等身人偶拍照、睡觉、举办婚礼。虚拟世界也激发她开始绘画生涯,在电脑上建模然后复制到现实中。
艺术家和世界对话从来没有这么直接,有网络的地方就有人与人、人与世界的连接,这是一个全新的命题。全球信息的同步、电子色、网络化、时尚消费、科幻散文的普及,深刻地嵌入这一代人的成长,并塑造了新一代虽相隔遥远却拥有相似现实的文化处境。很多创造者会拒绝自己被放入群体的队伍,然而这才只是多元主义的入口,走向深处我们就会发现原来这里是一个群落。
4
2021年,刘昕返回她的故乡克拉玛依,又前往塔克拉玛干沙漠寻找上世纪90年代的火箭碎片,创作了属于火箭残骸的故事《白石》,和《史记·天官书》形成互文。《白石》承载着物理材料、人类太空梦,以及中国的经济转轨等多条叙事线。《脱离》讲述了一个类似的故事,刘昕的智齿在自主机械生命体EBIFA的携带下进入了太空。在太空,智齿变成了一具新生的尸体,并向我们讲述了一个关于生命的故事。这些具有行动力、语言能力的物体就是她的动态雕塑,它们的生与死就构成了“宇宙代谢”。
刘昕任职于麻省理工学院媒体实验室。她视科学为一种有自身逻辑和韵律的语言,常常在科学和人文之间进行着翻译的工作,“二进制或是绳结计数,纠缠粒子或是一对恋人,基因测序或是占星术”。“万物都可以被分化,任何行为都有所源头。不幸又可幸的是,当我们看到最微小的量子、最宏大的宇宙,所有的答案又变成了一种猜测和图景。创造和被创造只是自然界里不断发生的解构和重组过程,一场永不停歇的循环。”她在一次采访中表示。
张季通过随性的创造反驳了存在于人与文字、与画画之间的单向交流,他的双向交流意味着“相信笔下的痕迹作为桥梁链接了未来的某个观者或者过去某个祖先的意志”。他的创作随感格外动人,“口诀每被念诵一遍,情绪就调动一次,意念就完成一次轮转,刻留在时空不会消烬;身上的洞口也随之一呼一吸,不停不息地运动着,如潮汐般温暖,皮囊下的暗涌唱诵着生命本身的旋律。”
这些艺术家试图突破科技的泛滥,寻找艺术的大标尺:他们借助具体创造但很快丢弃了具体,他们用并不系统的想法或者观念创造着系统,他们如此早地感知着、实践着可能。“一堵墙对另一堵墙说什么?”“转角/墙角见!”(Meet you at the corner!)这是“转角见!——首届当下青年艺术奖”借自塞林格《为埃斯米而作——既有爱也有污秽凄苦》的一对暗语。三十岁出头的“军士X”暂时性精神失常,过往的一切将他推向存在性黑暗中。翻开家里的书后,他不禁联想到,“父辈们、师长们,我在考虑‘什么是地狱’这个问题。我认为因为不能去爱而受苦,这就是地狱。”他在德文郡英国情报部接受专业培训,为反攻做准备,他和其他六十个人都不合群,任命上战场前一直能听到很多支钢笔在刮擦。叙事者交代,他曾打死一只小猫咪,“那猫是个间谍。你必须对准它使劲开抢。那是个披着件廉价毛皮的德国侏儒。因此绝对谈不上有野蛮、残忍、卑鄙,甚至是——”军士X的处境对我们时代的艺术家有映射关系。“不曾有哪一代人像他们那样,在职业生涯的起步阶段就被迫重新审视、理解和学习适应急剧变化的世界与生活,被迫面对一个加速逆转、局部动荡和全面危机的时代,一个极度压缩、市场化和投机的艺术生态。”
我认为,创造行为的发生是改造自己后的结果,也就是说一个人要创造新事物,必先创造他自己。而那些仅仅创造物,而没有创造自己的创造者,我称之为脱嵌的创造者。脱嵌既可以理解为人与其环境的分离,又可以理解为人与其环境的再组合,所以脱嵌既是崔灿灿所指的断裂,又是可能到来的重构。对于像我这样的环境检测者而言,脱嵌是一个信号——它意味着最重要的文化命题已经从宏观转向微观,从世界转向人。如何处理人的境遇、如何面对自己,才是我们首要面对的课题。这恐怕是个悖论:我们时代的艺术家就像将石头推向山顶的西西弗斯一样,他们会抵达,但也必然要重新开始。不过,这又有什么关系呢?历史也不过才刚刚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