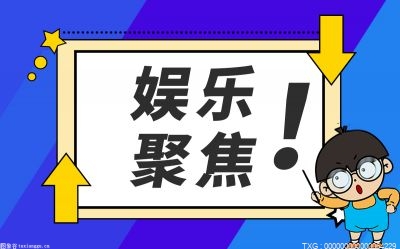和我差不多大的人(70年代中期出生),早年看片主要是从大银幕上来,但我一直不很贪恋影院效果。
目前还能成为影院的常客,一是工作所需,二是朋友相邀。我已经过了那种非某部电影非看不可,还必须前往影院看的阶段。所以无论是在北影节还是上影节,我不爱凑抢票这类的热闹。在电影节上看片,重要的是散场之后的相聚和开怀。
 (资料图片)
(资料图片)
国内的各类电影节基本跑了个全,别的城市几乎没有,我只在上海看过就在影院门口贩黄牛票的。具体说,就在上海影城每年那几位老爷叔。想来,每年的初夏时分他们都能尝到些甜头。
这样的景观,我幼时也领教过,只是更惨烈一些。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为了一张电影票大打出手是家常便饭,白刀子进红刀子出的战况也见过,但到了本世纪后这样野蛮的场景就看不到了。
还是在上海,那儿的人对日本电影有着特殊和浓烈的情感。《昼颜》曾被炒到2000元一张,而那年刚拿下金棕榈的《小偷家族》,更是夸张到一张黄牛票的标价能换上海郊区一套房的程度。
《悲情城市》在北京国际电影节上三秒售罄,而后被黄牛哄抬至8000元的涨停板,也还不算最离谱。
黄牛的想法很简单,漫天要价而已,我好奇的是真有挥金如土的人掏了腰包吗?如果有,这人是太爱侯孝贤这部电影了,一定要卡在这个时候,这个地点,方能一解相思《悲情城市》之苦?还是要想证明,他爱起电影来,是可以抛开一切的?
换做是我,情愿将这钱借给朋友,他若忘了还,当是送也行,我肯定不会拿这笔款去换一张戏票。
看电影的方式有很多种,我不想看遍世界上的所有电影,重要的或不重要的。我也不想拥有所有的观影状态。还可以说,电影从来就不是我的生命,我的生命是什么,我想我不到死的那一刻,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定义。
多年前,我写过一篇关于电影的长短句,就叫《我喜欢》。最后一句是:为了生活,可以一脚把电影踢开。我想只有这样,电影和生活才能保持平行,并能相互瞭望。应该说,我和电影的关系一直不紧张,这是我们能长相厮守的基础。有的聊就聊,没的聊就保持沉默。
我很少见到爱电影的人。当爱电影成为一种人生状态的证明,那就会将证明还给证明。比爱电影更重要的是爱,有了爱,爱什么都可以。如果恰巧是电影,也不必欣喜,就像你天天见到家人,不可能每天都满面春风,那是做戏,不是做人。
希望我以上的说辞,不会败坏诸君以各种方式进入《悲情城市》的心情。
无论怎样,这都是值得一看,并一看再看的电影。私下里,我对侯孝贤的赞美常常是滔滔不绝,但对于他这部极负盛名的大作,却很少提及。
《悲情城市》最早看的是碟片,后来在影院也看过。侯孝贤的很多杰作,我都一再重温。这部次数相对要少些,大概这一部太依赖于时代,而侯导另一些让我神游他方的影片,则浸淫于时间本身,更见容量,也更能飘散开去。而《悲情城市》像一件容器,水流进去就成了型。
《悲情城市》所指涉的「二二八事件」,引爆点是城管在警察的虎威之下,对烟贩收缴其所得而引发的逐级流血冲突。最终指向的是台湾光复后,外省人与本省人的矛盾。最近竟听到一种奇特的说法,指本片是为这起著名的历史事件洗白。
影片分为两部分,一个是林文良因参与走私,而让林家卷入黑帮械斗。另一个是林文清因亲近进步组织,而两次入狱。第一部分,被人戏称为是小津安二郎在拍《教父》,带出日本战败后的阴魂不散。
整个剧力的燃点,便是台湾本省人仍想将日元继续使用,而招至多米诺骨牌效应的杀戳不断。全片还大量运用了日本神风敢死队的誓词:你飞扬地去吧,我随后就来。
侯孝贤拍起动作戏,颇得布列松的神韵,用固定镜头,展现画内外空间的相互作用。人在运动,但却有一种静止的力量在限定着你的扩张。人物在出画入画之间,就是你生命摆荡之时。这在老大林文雄殒命之时,表现得尤为突出。
刀拼不过枪,本省人也敌不过外省人。而在林文雄丧命之前,他已有不祥之兆。他常常做梦,梦见自己被嗜赌的父亲绑在道旁,这是他最为沉重的童年阴影。当他子承父业坐在牌桌上时,他的大限也将至。
林文雄回忆梦境时,并没有出现与台词对应的画面。而林文清回忆童年往事时,便有了与他的述说相匹配的画面,这是个颇值得思量的现象。少年的他在模拟一个伶人的身段,顺便回忆他的耳膜所能得到的那些美好的回应。
而这段戏的声场处理却又是异常安静的,这仿佛也在暗示他的回忆不能得到全面的还原。林文清是聋哑人,他的语言系统不是手语,而是将所说的话落于笔端。若他要与时空进行更精微的对话,只能通过回忆,才能拼凑出他残存的声音形象。
这是全片里,我最喜欢的一场戏。不仅仅隐喻出台湾人,无论是外省还是本省人,数十年所处的失语状况。而是营造出声音之外的另一种响动,就像齐秦所唱的:贝多芬听不见自己的歌,我想听歌不一定要用耳朵。
在林文清回忆之前,他面前端座着深爱他的吴宽美。这是她的扮演者辛树芬最后出现在大银幕之上。素人出身的她,是侯孝贤电影发韧期最重要的形象,她人淡如菊、落花无语的形貌,是侯孝贤那些天高云淡的影片最为优美、最为深切的注解。她像多雾的清晨,像少人行走的小巷、像墨迹刚刚晾干的信封、像一个毋需解释的梦。
所以也有人说你只发自内心的喜欢辛树芬,你才能呼吸到侯孝贤电影那完全归属于画面的美。为了这个,这电影就应该多看几遍。
还有人玩笑说,这电影是为我而拍的。因我的笔名赛人来自于古希腊传说塞壬。由吴念真、张大春、唐诺、吴义芳等台湾文化名人所出演的一群知识分子正痛斥时弊。而另一边厢,吴宽美则用唱机放了一首与塞壬相关的曲子,并用笔写下了那个动人的传说。
一个空间,被隔成了两个区域,一个是一日逼近一日的现实,一个是一段拉近一段的过去,或者说是未来。最后,音乐声盖过了人声。
一种更令人憧憬的甜蜜,更让人心醉的奇境,弥漫在屋内,又飘荡在窗外。让那些慷慨陈词,也跟着失去了重量。我们的沉默,不是忧恐。而是在甚嚣尘上的声音之外,去寻找另一种与心灵相关的声场。
全片有大量的画外音,最主要的吴宽美的念白,她在写日记,她在记录生活的点滴,她的闽南语让那些凶险的日子多了些只可意会的静谧和淡然。
而另一种声音来自裕仁天皇和台湾当时的土皇帝陈仪,他们的声响与吴宽美阴柔的呢喃相比,丝毫不见阳刚,更多的是冰冷、机械和隐隐的胆怯。还可以说,吴宽美的自语有着再真实不过的内心起伏,而另两位大权在握的男人,则各有各的心口不一。
前面提到了侯孝贤对画外空间的运用,但最精妙的还是梁朝伟最后一次出场。他要照一张全家福,在摆弄相机时,他的眼神有些游离。他好像看见了什么?
影片借吴宽美的日记,告诉了我们答案,她说文清在被逮捕之前,仍在认真的工作,然后安安静静被带走。这哪里是工作,这就是无声胜有声的依依惜别。从美学上来讲,这就是声音对画面最为熨帖的补充。
太多人愿意将《悲情城市》当作一部具控诉意味的政治史诗来看,倘若将它视为爱情电影,或许会有更大的收获。
两个人在一起,总比跟另一些不知生命为何物的人在一起,要好得多。我最喜欢的台词,是在吴宽美在林家枯候之时,终于等来了林文清。乖巧的阿雪卸下四叔的行李箱,又极善解人意地为这对璧人取出纸笔,并俏皮地说道:你们慢慢写。
是的,你们慢慢写,我们慢慢看。这几乎成了《悲情城市》所给予我的全部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