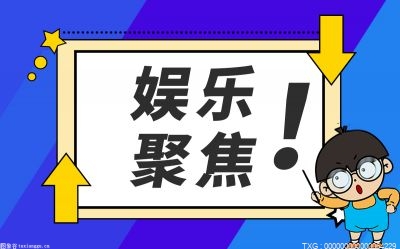现在是五月九日,中午,手机收到一小段截自万玛电影的视频:塔洛,那个讨不到老婆的牧羊人,正用藏语口音的普通话背诵《为人民服务》,喋喋喃喃,如念经,一字不漏,镜头间或指向一匹正在吮奶的羊羔:
 (资料图片仅供参考)
(资料图片仅供参考)
“……人总是要死的,但死的意义有不同,中国古时候有个文学家叫做司马迁的说过,‘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
《塔洛》
视频长度三分零七秒。我静静地看,忍不住笑起来,随即止住——万玛没有了。昨天中午我们都收到了这个不肯相信的消息。现在是夜里,演员黄轩发来语音。两个月前他还在青海与万玛拍片。他抽泣着,说:“我从未遇到他这样亲切的人,好像是我的父亲。”他明天就要飞赴拉萨,送别万玛老师。
去年万玛出版新小说集,要我作序。我从未议论过小说,但也就认真写了,因为我爱万玛的电影,他的电影的前身,便是小说。近期我的杂稿拟将出书,编排文档,收入这篇时,万玛倒下了,据说是忽然缺氧,不适,倒下了,五十三岁。
我爱万玛的电影。虽然不具备评论的资格,但我看了万玛的几乎每部作品。我愿斗胆说:内地没有这种导演。内地电影的种种手法、招数、兴奋感,在他那里,都没有。他有的是什么呢?昨天闻知噩耗,我心里一遍遍过他的电影,包括《塔洛》。
那是部黑白电影,一上来就是整段背诵,之后,万玛开始平铺直叙——为什么再难看到老老实实平铺直叙的电影啊——直到憨傻的塔洛人财两空。这样的结局,稍不留神就会拍坏的,我想,万玛怎样收束呢?只见塔洛骑着乡下人的破摩托往山里开,开着开着,他停下来……停下来干嘛呢?请诸位找来看吧,不剧透。
《静静的嘛呢石》,他的初作,太朴素了,我猜院线根本不会要,但我还想再看一遍,看他如何平铺直叙——如布列松的《穆谢特》(Mouchette)、特吕弗《零用钱》(Small Change),甚至,奥尔米《木屐树》(The Tree of Wooden Clogs)那样的平铺直叙——片尾,男主角,那位当了喇嘛的孩子,从山梁(长镜头自银幕左侧跟着他)一路小跑着,几度被树丛遮住,又露出身影,又被遮住,最后蹦跳着,奔进寺庙,庙里一片嗡嗡的诵经声,孩子迟到了,电影就结束了。
《静静的嘛呢石》
他的电影期待和那孩子一样纯良的观众(小喇嘛在电视里看了《西游记》,大为着迷)。这样的观众,应该有吧。我跟万玛要了在片尾字幕间播放的诵经歌的音频。一个小小男孩口齿不清的呢喃。现在这首歌还在手机里。不因为我对藏传佛教的兴趣,而是,我听着,发现有一种心里的光亮,很早很早就失去了,没有了。后来放听过两次,没再听。人会害怕被这种(孩子的嗓音唱出的)片刻所提醒,提醒你早已不再天真。(文末可收听)
《寻找智美更登》的智美,是古老藏剧中的王子,为救助穷人,献出眼珠。在万玛的故事里,这部藏剧将要拍成电影,摄制组找了担任女角的美丽姑娘(她倚在门口,怯生生唱了几句,好听的吓坏人),她说,非得是与他合作的那位男演员,才肯出山,而其实男演员曾是她的相好,掰了之后,远去别地教书。现在,姑娘路远迢迢跟了车去,就想讨个说法。
摄制组不知情,带她上路了,途中,前座的男子大谈自己失败的恋爱,后座的姑娘默默听着,想心事。一程又一程,总算到了,青年从办公桌后起身迎客,被告知跟着的是她……接下来,你以为是伤心姑娘与负心郎的激烈对话吗?不,万玛没这么做。镜头移向挤满学生的操场,很远的远处,篮球架下,站着那对恋人。
太多女生有过相似的遭遇(男生也是),但我们不知道他俩说了什么,不知道姑娘有没有讨到说法,更不知他俩是否再次合作……下一组镜头,姑娘一声不响回了来,随车离开。
万玛懂人,就此一幕,我以为他很懂电影。
《寻找智美更登》
再就是院线也不会要的《老狗》。万玛读过屠格涅夫的《木木》吗——福楼拜说,那是世界上最动人的小说——但“老狗”的命运和《木木》的故事,完全不同,因此,不是动人,而是,当我眼看老头子慢慢在木柱上绑定老狗,转过脸,扯平绳索,拉紧了,一步迈一步走……我从座位上直起身,不知如何是好。
《老狗》
领教万玛的第一部电影,是《撞死一只羊》。主角,那位彪悍的寻仇者想象他挥刀砍去。这时,万玛用了一组模糊的放慢的镜头,其实什么都没发生(这是看懂经典小说,自己也写小说的导演才会使用的伎俩)。记得那位司机的相好,驿站老板娘吗?万玛真会调教演员,在他下一部电影《气球》中,这位活色生香的女演员忽然变成老实巴交的农妇,若非万玛告诉,我认不出她就是那位老板娘。
接着,是《气球》——这次,失恋的姑娘变为尼姑,意外遇见前男友,而男友已将他俩的恋爱写成书。她多想读这本书啊,却被老实巴交的姐姐一把扯去,扔进炉膛烧了(那位狼狈的前男友回答姐姐的斥责时,眼镜忽然掉下来)——万玛此前几部作品的性格在其中汇合了,更具规模与野心,但他的叙述,同样沉着。当孩子举着气球奔去,消失在山丘的那一头,接着,气球升了起来(多么成功的运镜),万玛似乎找到了他的电影的新维度。这维度预示他未来的电影可能企及的高度,但他死了。
《气球》
现在,我等着看黄轩出演的《陌生人》,那是万玛的遗作。黄轩说,他在一组镜头的拍摄中,迎对群山,泪流满面。他的意思是说,现在想来,难道他预先为万玛痛哭了吗?今天中午,十号,黄轩来语音,说他见到了被布帘隔开的万玛(像是睡着了,很安详),明天起灵,很多很多送行者将簇拥着万玛,在大昭寺诵经后,绕行拉萨。藏民相信,死在拉萨是至高的福分。
沉静、内敛、谦和,万玛的相貌与气质,是我见过的导演中最像知识分子的。他的想象,他的内心,他以内地习得的一切而回看西藏的眼光,都交给了电影,我在他的每个角色中,都看见他,几次与他对坐,我想:这个脑袋在想些什么?《气球》公映后,我问他,拍摄正在交配的羊,多难啊,你怎么弄?他轻轻地说:还好,有办法的。问他爱看什么书,他说,和文学与电影无关的书。问他孩提时代在村里看的电影,他提及卓别林。啊,卓别林!我因此明白他何以忠于并懂得卑微的灵魂,却不渲染哀苦,而是,使人发笑——因极度淳良而引发的那种笑,在他的影像中,令我发笑的片刻都带出万玛的性格,沉静、内敛、谦和。
他提携的好几位青年如今都成为导演,包括他生气勃勃的公子。此刻他们该多难受啊。难受的日子还在后面呢!是万玛让西藏被听到,被看见,他那讲到一半的故事,当然会继续,但讲述者不再是万玛才旦了。
他站在那里的样子,多善良,多好看。前年,他远来京郊参观我的西藏组画展览,我不感到荣幸,反倒羞惭。那些画只是短暂的一瞥,我对那片高原的了解其实是肤浅的,万玛的电影,才是西藏的血肉。一个民族拿出自己的电影,面对世界,便有了无可言说的容颜与自尊,万玛,是践行这自尊的第一人。
2023年5月9日—10日
万玛才旦,1969年12月3日—2023年5月8日